截止到2018年,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·斯诺的经典纪实作品RED STAR OVER CHINA《红星照耀中国》(曾用译名《西行漫记》)已经出版有81个春秋。回溯这本书的出版过程,就像斯诺进入陕北的经历一样,在激情浪漫中充满了坎坷曲折。80多年中,基于原著,在中文语境中以雏形本、全译本、节译本、抽印本、内部参考本等形式出版了不少于60种版本,拥有极为庞大的读者群体。1938年胡仲持等十二人翻译、复社的《西行漫记》版,激励了无数国统区的革命青年去往延安;1979年董乐山翻译、三联书店的《西行漫记》(原名《红星照耀中国》)版,在上世纪80年代的知识分子群体中,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时至当下,董乐山译《红星照耀中国》进入初中语文教材,以其独有的睿智思想、时代特色和语言魅力让新时代的青少年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历史。
斯诺在延安采访毛泽东
斯诺著《西行漫记》1937年英文初版
复社版的《西行漫记》是斯诺这部不朽名著的第一个正式中译本,由王厂青、林淡秋、陈仲逸、章育武、吴景崧、胡仲持、许达、傅宗华、邵宗汉、倪文宙、梅益、冯宾符12人分别翻译并在版权页署名,由胡愈之统稿校订。这12位译者是上海孤岛文学时期“星二座谈会”的成员,据新华出版社《胡愈之传》记载,“陈仲逸”是胡愈之的笔名;胡仲持为胡愈之的二弟;傅宗华、倪文宙、吴景崧、冯宾符为胡愈之在商务印书馆的同事;林淡秋、邵宗汉、梅益是胡愈之在《译报》时代的同事。许达是斯诺在中国的秘书,实际为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地下工作者郭达。另外,有部分资料指出,王厂青应为粟裕的秘书蒯斯曛的化名,此处存疑。
在1979年第一期《读书》杂志上,胡愈之回忆了这次让他激动而紧张的译事:“有一天他(斯诺)说,刚得到英国航空寄来他的一本著作的样本。外国出版社有规矩,要把印出的第一本样书送给作者审查,所以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。我就向他借阅。他答应了,但说只有一本,看完还他。这就是后来闻名世界的《西行漫记》的英文原本。”
这段话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,复社版《西行漫记》的英文原本为英国1937年“左派”出版社维克多·戈兰茨公司的版本,这一版本的原文与1938年复社以《西行漫记》为名,正式出版的版本有不少明显的出入。张小鼎先生在《〈西行漫记〉在中国的流传和影响》一文中明确指出:“此书虽据伦敦‘红星’初版译出,但复社出版时,斯诺对原著的文字又作了少许增删,就是说,复社实际是照作者的‘修正本’译出的。”对照1937年英国原版不难发现,较为明显的是复社版删除了原书第11章的第5节。另外,此书英文版完成于1937年7月下旬,因1937年8月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,斯诺在复社版《西行漫记》中对国共两党的表述作了修改。
作为老一辈的新闻人,胡愈之对时局有着敏锐的判断。尽管他认为这是一本难能可贵的书,但他还是向上海中共办事处的刘少文同志了解斯诺的具体情况。刘少文来自陕北,对斯诺这段采访了然于心。在得到他的认可后,胡愈之组织力量开始翻译出版。
斯诺这部纪实作品的译名,在当时做了策略性调整。据胡愈之回忆:“斯诺的原书名直译过来是《中国天空上的红星》,在当时的情况下当然不能照译。我们就改用一个隐讳些的书名。为什么要叫《西行漫记》?因为在工农红军长征以后,关于我们党在西北情况的比较真实客观的报道,只有一本书:范长江同志写的《中国的西北角》。范长江同志当时是《大公报》记者,他跟随国民党部队去了西北,写了一系列关于红军的报道,后来集印为这本书,限于当时条件,不能写得很明显,但是已经很受欢迎了。从此,‘西’或‘西北’就成了我们党所在地的代称。《西行漫记》这书名,一般人看了就可以联想到我们党。”同样,十二位译者之一的倪文宙在《忆念鲁迅师》一文中也有过关于类似的说法,他认为:“改名为《西行漫记》进行翻译,局外人以为这是本小说或是游记书,不容易一下认出这是一本‘红色’的歌颂解放区的书,容易在社会上通过。”
胡愈之得到此书并组织翻译的时间在1937年12月,到1938年1月得以出版,得到了斯诺重要的帮助。《西行漫记》复社版第15页中,斯诺表示:“现在这本书(RED STAR OVER CHINA)的出版与我无关,这是由复社发刊的。据我所了解,复社是由读者自己组织起来的非营利性质的出版机关。因此,我愿意把我的一些材料和版权让给他们,希望这个译本,能够像他们所预期的那样,有广大的销路,因而对中国会有些帮助。”正是在这样的想法下,除了原书已经修订意见,他还提供了1937年戈兰茨版都没有的20张照片。
正如斯诺美好的愿望,由当时商务印书馆工人承印的《西行漫记》甫一问世,初版顷刻脱销,当年即加印四版。香港的出版社翻印了许多,远销南洋。《西行漫记》在当时中国产生的影响超越了世界任何一个国家,进步青年辗转传抄,把《西行漫记》看作身家性命一般,怀揣梦想奔赴延安。
从图书出版角度而言,真正赋予了斯诺这本不朽名著以《红星照耀中国》的书名的,是译者董乐山。
在RED STAR OVER CHINA真正以《红星照耀中国》面世之前,在中文语境中,它以《西行漫记》以及纷纭繁复的译名产生过两次出版高峰。一次为1937-1938年间,这个时期以王福时等翻译、北平出版的《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》为开端,以复社版《西行漫记》为最高峰;一次是1946-1949年,这一时期它的面世,多围绕毛泽东进行,自1946年国际出版社出版的《毛泽东自传》开始,以1948年大连复社再版《西行漫记》与1949年上海启明书局出版的《长征25000里——中国的红星》为高峰,后者为多人新译,根据1938年7月美国版译出。
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,由于国际国内局势等诸多原因,直到1979年三十年间,中国内地没有公开出版过斯诺的这部作品。唯一一次内部出版,是在1960年,当时正值斯诺访华。这个版本由人民出版社的副牌三联书店推出,印量极少,没有公开对外发行。
检索中图版本及《1949-1986全国内部发行图书总目》,RED STAR OVER CHINA第一次以《红星照耀中国》书名出现,是在1984年新华出版社出版的《斯诺文集》中,此文集中《红星照耀中国》采用的是董乐山的译本。1979年三联书店正式出版的董乐山译本,仍旧以《西行漫记》为主书名,封面标注(原名《红星照耀中国》)。
作为一本对毛泽东及中国共产党早期历史有重要论述的著作,《红星照耀中国》以原名直译面世,必然也代表了意识形态宣传口径的意思。在1984年出版的《纪念埃德加·斯诺》一书中,董乐山先生撰文《斯诺和他的〈红星照耀中国〉》,谈到了这次三联书店的组稿过程:
1975年冬,三联书店总经理范用来约我重新翻译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·斯诺的《红星照耀中国》一书,我欣然从命,因为,对于我来说,它的意义远远超过了翻译一本名著。
那天,我与范用的谈话情不自禁地转到了1938至1939年间我们分别在重庆和上海初次读到《红星照耀中国》的欣喜若狂的情况。虽然经过了战争年代的颠沛流离,范用至今犹小心翼翼地保存着40多年前出版的初版中译本。“是红布硬面的精装本”,他特别加了一句。由于当时的政治环境,这个中译本1938年2月在上海出版时,并不叫《红星照耀中国》,用的是一个隐晦的书名《西行漫记》。
这段写于1982年的文字传达出了两点信息:第一,RED STAR OVER CHINA的新译策划工作在“文革”结束前就已经开始;第二,在此之前,在出版物中,RED STAR OVER CHINA没有使用《红星照耀中国》的译名。
董乐山自1949年来北京工作后,一直从事着新闻类题材的翻译工作,1961年与其他几位译者一起,受命翻译美国记者威廉·夏伊勒的纪实作品《第三帝国的兴亡》,此书于1963年在世界知识出版社以“灰皮书”的形式内部出版。在1975年,才独立接手翻译斯诺这部作品,他在《我的第一本书》中自己陈述,《西行漫记》是他从事职业翻译30年后才出版的一本可以称得上个人劳动成果的东西。这本书的正式出版时间为1979年。
三联书店的编辑沈昌文主要负责1979年版董乐山版《西行漫记》(原名:《红星照耀中国》)的编辑工作,在其作品《八十溯往》中,他这样回忆了这段组稿过程:“到了七十年代末,我受命组译《西行漫记》时,自然觉得,这工作非老董(董乐山)来做不可。”对于董乐山译本的评价,作为编辑,他既是第一读者,也是第一批评人,他认为:“重译《西行漫记》,可说是吃力不讨好的工作,可是老董毫无怨言地卓越地完成了。我们现在可以说,这是三联书店出过的优秀译品之一。”
作为一名具有职业追求的翻译家,董乐山在《红星照耀中国》的英文版本上选取也有自己的考虑。RED STAR OVER CHINA在1937年初版之后,埃德加·斯诺做了反复的修订,其主要版本有英国戈兰茨版(Victor Gollancz 1937),美国兰登书屋初版(Random House 1938), 美国兰登书屋第一次修订版,美国兰登书屋第二次修订版(Random House 1944),格罗夫增补修订版(Grove Press 1968),英国戈兰茨增补修订版(Victor Gollancz 1968),企鹅出版社鹈鹕丛书版(Penguin Books 1972)。斯诺随着时局的变化以及自己对于中国共产党的理解,修订增删这部经典作品,每一个版本相较上一个版本,都有不仅仅是字句和表述上的调整。在中宣部出版局、三联书店及翻译家董乐山经过慎重考虑和论证后,决定根据1937年的初版本译出。三联书店编辑部在该书《出版说明》中谈道:“我们深信,广大读者是会用分析的态度和历史的眼光看待书中的问题的。”
1979年12月,在经历了《读书》《出版工作》《新闻战线》等报纸杂志近一年的预热后,董乐山译本《西行漫记》(原名《红星照耀中国》)正式出版。在这一年当中,据不完全统计,与斯诺相关的文章就有《解放“内部书”》(雨辰著 《读书》1979.1)、《胡愈之谈〈西行漫记〉中译本翻译出版情况》(胡愈之口述 三联书店整理《读书》1979.1)、《做斯诺式的记者》(白夜著 《新闻战线》1979.1)、《谈〈西行漫记〉及其他》(尼姆·威尔斯著 王福时译《读书》1979.3)》《〈西行漫记〉在中国》(张小鼎著《出版工作》1979.5)、《在斯诺的小客厅里》(陈翰伯著《读书》1979.5)等等。其中,和开上世纪80年代读书风气之先河的著名文章《读书无禁区》发在一起的《解放“内部书”》,更是在文末明确指出:“照老框框本要内部发行的《西行漫记》、《尼克松回忆录》,也决定公开发行。”这一切为董乐山翻译的《西行漫记》(原名《红星照耀中国》)的出版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。
2001年,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了四卷本《董乐山文集》,第一卷的最后一幅插图,即是1984年董乐山为《西行漫记》(原名《红星照耀中国》)写的译后缀语的部分手稿。可以清楚地看到,董乐山最一开始的手迹为“《红星照耀中国》译后缀语”,后来修改成“《西行漫记》译后缀语”。我们无法还原董乐山真实的内心轨迹,这只是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他一次纠结的表征。RED STAR OVER CHINA中的over,在英文初版本中本是一次并不太小的印制事故——斯诺给它定的书名本是RED STAR IN CHINA,却不小心被排错了。这是一次让斯诺拍案叫绝的印制事故,over一词恰恰是这个书名最神来之笔。在《英汉大词典》over的词条中,它有笼罩,(势力)在……之上的意味。《西行漫记》的译名,是具有历史特色的策略性结果,毕竟只有让这本书在1938年出版了,才会有更多的进步青年了解中国共产党。《红星照耀中国》的译名则不同,它既近乎完美地表达了英文的本意,又呈现出了一种蓬勃且不可阻挡的势,恰恰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最准确的写照。
1984年,《斯诺文集》由新华出版社出版发行。这本让斯诺纠结修改了近乎大半辈子的作品,第一次在中文语境中,是董乐山以图书这一正式出版物为载体,赋予了它近半个世纪前就应有的名字——《红星照耀中国》。 “部编本”语文教材上有一段胡愈之推荐《红星照耀中国》的文字,这段文字是胡愈之为董乐山新译本写的。他在文中热情推荐出版于1979年的董乐山译本,同时在文中对1938年“复社版”的部分问题做了说明。
在今天,《红星照耀中国》被收入中学课本,以忠实的原貌走近更广大的青少年读者。
来源:光明日报(作者:刘健,系北京外国语大学比较文学博士)
公众号:pcren_cn(长按复制)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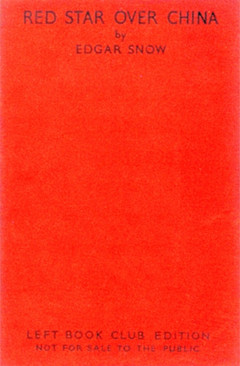

评论